|
www.bazaarmadrid.com http://www.bazaarmadrid.com/ 原文插图 原文截图 本文作者像 民主世界的“涡轮瘫痪” 弗雷迪·格雷(Freddy Gray) 我们是生活在强人时代,还是在弱人时代? 迄今为止,人们将二十一世纪的政治厘定为在全球范围内偏离自由主义(不论那是什么)而转向威权主义,这一趋势以俄罗斯的普京、土耳其的埃尔多安、印度的莫迪、匈牙利的欧尔班、巴西的博索纳罗、菲律宾令人快乐的杜特尔特为代表。但在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在我们理当更发达的民主国家,政治的主调却是领导核心的软弱和失败。(本段删去一个名字。——译注) 什么样的世界之王不能非法地吃蛋糕? 环顾一下世界。 人们经常指责鲍里斯·约翰逊一心想成为独裁者,是个急于实现童年时代“世界之王”幻想的自大狂。看上去进展不是非常顺。 上周(6月6日——译注),他祈求保守党不要“追随媒体的调子起舞”,在信任投票中支持他。41%的保守党议员对他的恳请置若罔闻。与前任特雷莎·梅(Theresa May)相仿,约翰逊在投票中涉险过关,但眼下人们普遍认为,他的领导地位已岌岌可危。为保住自己的首相职位,一位拥有八十个多数议席的首相,眼下必须迎合保守党各派系,而他一度认为,他们支持他是理所当然的。 这位英国政坛赫赫有名的桀骜不驯之人已被迫就范,这主要是因为他破坏了那些他为更普通人士引入的微不足道的封控规则。什么样的世界之王不能非法地吃蛋糕呢? 在美国,乔·拜登的权威已经败坏。本周,民主党的进步派优雅明星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在有线电视新闻网里露出一丝坏笑,她拒绝证实自己将在2024年大选中支持总统。 她的不情愿容易理解。拜登的民调数据持续恶化:目前支持率为39% (在担任总统的同一阶段,唐纳德·特朗普支持率为44%)。假如像每个人都预料的那样,民主党人将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惨败,那么拥有国会多数地位的共和党人大有很可能弹劾这位民主党统帅,以报复民主党人对特朗普的两次弹劾。对碰巧是反对派控制众议院的任何总统来讲,弹劾或许很快就将成为常态。 同时,西班牙和荷兰政府都因电话窃听指控而深陷窘境。上周在瑞典,首相玛格达雷娜·安德森(Magdalena Andersson)在一次事实上的信任投票中勉强过关,她已因未能处理好涉及移民的犯罪问题而饱受攻击。 “我们有必要竞选文本上下功夫。” 原文插图 在贾斯汀 · 特鲁多( Justin Trudeau )和杰辛达 · 阿德恩( Jacinda Ardern )领导下,加拿大和新西兰似乎有了两位上镜的中间派人士掌权,他们可以抵制全球性的反政治趋势。国际媒体时常高度赞扬贾斯汀和杰辛达(他们看起来关系不错),他们都得益于严格实施封控措施而收获的最初民望。眼下,两人都没有处于强势地位。去年 9 月,特鲁多在未获多数票的情况下再次当选总理。本月早些时候,在安大略省的省级选举中,他所在的自由党仅赢得了一百二十四个席位中的八个。 在本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德国和以色列都被一个政治人物主导。安格拉·默克尔的总理任期跨越了十六年,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最近一次担任总理持续了十二年。但眼下,软弱而分裂的执政联盟取代了安吉拉和本杰明。新任德国总理奥拉夫·肖尔茨(Olaf Scholz)的支持率仅为30%。他所在的社会民主党在民调中下滑至第三位。随着内塔尼亚胡计划再次卷土重来,以色列的左右联盟似乎处于崩溃的边缘。 周日(6月12日——译注),意大利一些地方举行了选举。后法西斯政党“意大利兄弟”(Brothers of Italy)表现良好。但意大利是一个奇怪的例子。 另一位前欧盟技术官僚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目前担任非民选总理,其支持率高得惊人(尽管有所下降),达到55%。这可能是因为他在响应大流行病过程中成功展示出了一种控制感。或者也可能是,在这段不可思议的反民主日子里,人们往往会喜欢上他们没有选择过的统治者。(请留意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持久民望。) 尽管如此,在明年的选举中,预计德拉吉的紧急民族团结政府仍将被取代——就目前情况而言,很可能是由意大利兄弟、北方联盟(Lega Nord)和意大利力量(Forza Italia)组成的右翼联盟取代。这样的结果,即用民选政府取代非民选政府,将被绝大多数国际媒体视为民主的灾难。 进步派人士往往辩称,鉴于大男子主义独裁者严重困扰着人类,民主国家将受益于全球领导层中出现更多女性气质。在一个大量男性被认为是女权主义者的世界,让更多女性掌权或许有道理。但阿德恩的经历、5月的失败以及默克尔留下的分裂遗产表明,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改善性别平衡不一定是这个世界诸多难题的答案。假如下一位赢得权力的女性是意大利兄弟的女性领导人乔琪娅·梅洛尼(Giorgia Meloni),我们不会听到许多女权主义者的欢呼。 对中左翼的恋欧人士来说,“基于规则”的秩序的最后也是最大希望,是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他刚刚轻松赢得连任。不过,马克龙上周末也经历了一个痛苦时刻: 在上周日的第一轮议会选举中,他的表现比自1997年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以来的任何一位法国总统都要糟糕。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的直言不讳令人钦佩,由他领导的法国新极左翼联盟Nupes眼下可能妨碍总统的第二个任期。 面对一个碍事的立法机构,马克龙的解决方案可能是组织一系列精心挑选的“公民集会”,赋予他的立法议程以民主批准的表象——假如由某位右翼民粹主义者提出,如此典型的独裁举动将在世界范围内引发惊恐万状的斥责。 法国极左翼联盟Nupes领导人让-吕克·梅朗雄。图源:Getty Images 假如能够成功处置另一个“项目恐惧”,在周日的议会选举第二轮中,马克龙或许就能避免更进一步的尴尬。这在总统选举中对他已经奏效了。尽管马克龙不受欢迎,但他有理由相信,绝大多数法国人将第三次拒绝肮脏的民族主义者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未来数日,他将努力团结法国的温和派,以及那些通常不会支持他,但足够富裕,因而惧怕梅朗雄再分配目标的人士。 (在6月19日举行的法国国民议会选举第二轮投票中,马克龙所在的中间派联盟获得577个议员席位中的234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但未能达到绝对多数席位所需的289席。梅郎雄领导的新左翼联盟获得124席,将成为最大反对党。马琳·勒庞领导的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获得89席,成为议会第三大党。——译注) 民主政治变得越来越消极 称其为“恐惧更糟事项”因素吧,那是很强效的。 我们本应处于民粹民族主义和自由国际主义之间的全球性民主斗争中。但在英国、美国、意大利和法国(只提这四个国家),没有一个国家的民主运动看上去能维持民主的多数。因此,民主政治变得越来越消极。候选人获胜,不是因为他们是谁、代表什么,而是因为他们不是谁、反对什么。马克龙不是勒庞。约翰逊不是科尔宾。拜登不是特朗普。特朗普不是希拉里·克林顿。(科尔宾,即Jeremy Corbyn,生于1949年,现英国工党国会议员,前工党领袖。——译注) 结果就是美国学者迈克尔·林德(Michael Lind)所称的“涡轮瘫痪”(turbo-paralysis)。他写道:“我们可能要在一个无法重建的旧体系和尚未建立起来的新体系当中,陷入一段旷日持久的中间过渡期。我们或许不得不忍受数年没有行动的活动和没有运动的动议。”(迈克尔·林德,生于1962年,现任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林登约翰逊公共事务学院教授。——译注) 在这种环境下,政治人才库变得越来越了无生气。鲍里斯·约翰逊上周坚持留任,一个主要原因是,尽管保守党方面越来越担心眼下他在选举中有害,但他们想不起比他更好的人选了。此外,假如首相宣布提前选举,他仍有合理机会获胜,这主要是因为他的对手将是基尔·斯塔默(Keir Starmer)。(基尔·斯塔默,生于1962年,现任英国国会议员,工党领袖。——译注) 同样,阻止共和党人推动弹劾拜登的可能是这样一种担忧:民主党人可能加入这个有趣、无用、毫无指望的老乔行列,为的是在2024年之前找到一个更具活力、更具魅力的候选人。不要在敌人犯错误时打断他,诸如此类。不过,副总统贺锦丽比拜登受到更广泛的厌恶。在贺锦丽之后,接替乔的下一个热门人选是交通部长彼得·巴蒂吉格(Pete Buttigieg),2020年他竞选总统时,在非洲裔美国人选民中的民调支持率为零,这一点广为人知。 说我们正面临民主领导的危机,这并非什么了不得的启示,但我们很容易忘记,这一问题有多么深刻和广泛。早在新冠病毒长出丑陋的蛋白刺突之前,败坏就已开始。它是在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的反恐战争失败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发展起来的,这两次危机都消耗了大众和精英之间的信任。 起初,新冠病毒实际上可能改善信任赤字:受惊吓的人们转向他们的领导人寻求希望。除了唐纳德·特朗普这个明显的例外,世界主要领导人在着手应对病毒时,都享受到了一种战时性质的人气反弹。几个月时间里,情形似乎是这样:某位领导人越是急于要废除基本的民主自由以“阻止病毒扩散”,他或她的民意支持率就攀升得越高。 2020年3月22日,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在每日疫情简报发布会上发表讲话。图源:Getty Images 约翰逊的自由放任本能意味着他对实施封控态度犹豫,于是,他发现自己的支持率下降了。后来,在实施封控、他本人几乎死于新冠病毒后,他的工作支持率飙升至最高水平。同样,在危机自由主义颠三倒四的世界里,选民似乎对剥夺他们自由的领导人最为热情。评论家们对威权国家可以强令人们待在室内的优势报以热切关注。(最后一句有删节。——译注) 与此同时,人们普遍同情那些不得不面对如此不可能的公共卫生问题的自由世界领导人。眼下,在这个后大流行病的世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那种齐心协力的不可思议的爆发已消失殆尽。群众的怨恨又回来了,而且是报复性的。 在所有地方,人们对实施封控的巨大成本的早期愤怒都在加剧。我们看到,数以百万计的儿童正努力跟上教育进度,新冠疫情之后的一种虚无主义正在迫近,人们对这些事情越来越愤怒。在发达世界的城市中,暴力犯罪持续上升。 通货膨胀正在撕裂我们的社会和政治结构。西方领导人热衷于将生活成本飙升归咎于乌克兰战争。但选民就是消费者,而且我们都知道,早在“普京涨价”之前,物价就已经开始飙升。 在英国、美国、加拿大、意大利、德国、瑞典、西班牙和荷兰,通胀率目前在6%至9% 之间。生活水平正迅速下降。所有这些国家的政府现在都发现自己承受着巨大压力,这并非巧合。民主世界上一次面对这样严重的通胀螺旋,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那十年间,政治生活也中出现了类似的波动。从1972年1月到1981年1月,美国有四位不同的总统。七十年代,英国举行了四次大选,有四位不同的首相。 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威权铁腕人物在对抗通胀方面甚至更为笨拙。在埃尔多安领导下的土耳其,通胀率已达到灾难性的73% (一些估计给出了更高的数字)。在博索纳洛领导下的巴西,通胀率为12% ; 在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通胀率为17%。 没有领导人预料到会出现如此剧烈的通货膨胀。政客们认为,他们可以借入无限量的资金而不受惩罚,并相信,一旦大流行病结束,经济将以某种方式恢复正常。他们现在发现自己错了。各国政府的选择是,要么加税,要么削减成本。两者都令人痛苦且不受待见。英国内阁的一位资深成员表示:“我们需要一个可以抵达春天的冬天。”祝他在家门口兜售消息顺利。 更大的麻烦在于,选民和政治系统无法忍受我们现有的自由派领导人——但我们也担心一个不自由的未来。选民在他们不信任的拙劣统治者和他们不信任的危险叛乱分子之间左右为难。民主世界似乎陷入了困境,或者说陷入了涡轮瘫痪:从一场危机到另一场危机,方向转变迅捷,却茫无头绪。 (作者是英国《旁观者》周刊副主编。本文原题“The death of political authority”,见于《旁观者》周刊,2022年6月18日出版。译者听桥,为原文加上小标题,并有多分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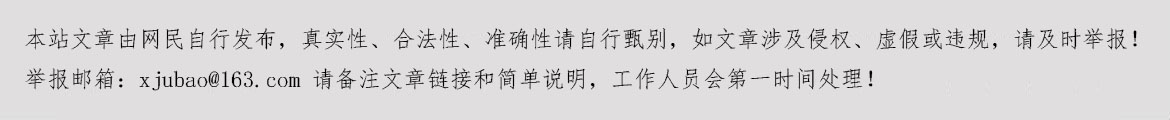
|
 鲜花 |
 握手 |
 雷人 |
 路过 |
 鸡蛋 |
分享
邀请